金鸡奖提名心惊胆战,周政杰:表演中永存“少年”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# 棱镜:一个演员的自我勘探
那束光打下来时,周政杰首先感到的是惶恐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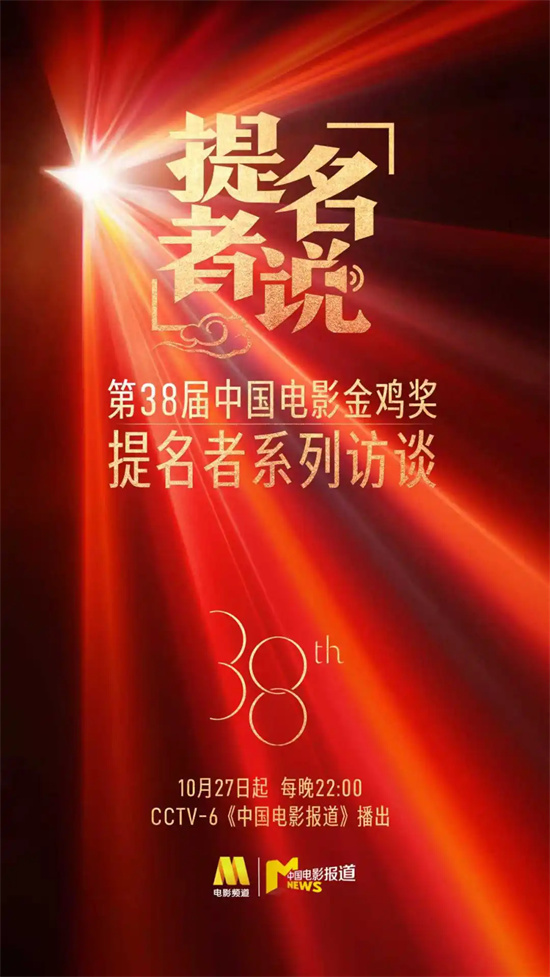
《中国电影报道》“提名者说”的录制现场,空气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。这个刚凭借《老枪》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年轻人,用“害怕”形容自己的初反应。“金鸡奖是每个中国电影人心中的圣殿,”他说,声音里有种小心翼翼的珍重,“这种害怕不是退缩,而是一种敬畏。”
这份敬畏很快转化成了动力。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奇特的临界点上——恐惧与渴望同等强烈,它们相互挤压,竟在缝隙里生出光来。
**一**
《老枪》的剧本吸引他的,正是这种临界感。故事里,少年耿晓军与老警察老顾之间横亘着整个时代。那不是简单的代沟,而是两种生存哲学的剧烈碰撞。
“耿晓军是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。”周政杰这样解读他的角色。那个少年活在自己的乌托邦里,对成人世界既抗拒又向往。他渴望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大人,却发现现实中的成年人早已放弃了理想。这种撕裂感,让角色呈现出一种近乎悲壮的固执。
最难忘的是那场对峙戏。耿晓军与老顾在废弃工厂里,少年嘶吼着“开枪”,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。那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而是一场多声部的合唱——老顾的愤怒、其他警察的惊愕、耿晓军自己的绝望,所有这些情感交织成网,每个演员都在网上颤动。
“好的表演是相互成全的。”周政杰说。那一刻,他不再只是扮演耿晓军,他就是那个被困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少年。
**二**
某种程度上,周政杰在耿晓军身上看见了自己十八九岁时的影子。
“那时候面对不公,我也会倔强,会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反抗世界。”他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对过往的宽容。不同的是,耿晓军选择了偷枪这种极端的方式,而周政杰选择了表演。
他欣赏耿晓军的“少年勇气”。那种不计后果、不问得失的纯粹,在成年人的精打细算里显得如此珍贵。虽然他知道偷枪是错的,但他理解那种绝望——当你所有的语言都失效,当你被整个世界误解,你只能抓住一件实在的东西,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这种理解不是来自技巧,而是来自记忆深处那个同样倔强的自己。表演最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:你既在创造别人,也在重新发现自己。
**三**
谈到表演追求,周政杰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:“我想成为那种远看光滑,近看有棱角的演员。”
远看光滑,意味着不刻意炫技,不让表演显得突兀生硬。你的角色应该自然地活在故事里,成为叙事肌理的一部分。但近看要有棱角——那些精心设计的细节,那些微妙的情感变化,那些只有细心观众才能发现的匠心。
这很像中国画里的皴法,远看是浑然一体的山石,近看却是千变万化的笔触。好的表演应该经得起这种由远及近的审视,在不同的距离上呈现不同的美感。
在《老枪》里,他努力实践这种理念。耿晓军表面上看只是个叛逆少年,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眼神,会发现里面有太多东西:对父辈既崇拜又失望的矛盾,对理想既坚持又怀疑的摇摆,还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。这些细节像水下的暗流,让角色变得丰富而立体。
**四**
访谈接近尾声时,周政杰又回到最初的话题。金鸡奖120周年的特殊节点,让这次提名有了更深远的意义。
“每个提名者都是一座桥梁。”他说。一头连着中国电影的辉煌传统,一头通向无限可能的未来。压力从来都在,但真正的创作者懂得如何将它转化为艺术前进的动力。
离开录制现场时,周政杰回头看了看那束光。它还在那里,明亮而温暖。他知道,恐惧不会消失,但与之共处的方式会越来越成熟。就像耿晓军最终要与世界和解,他也要学会与演员这个身份带给他的所有惶恐和荣耀和平共处。
远看光滑,近看有棱角——这不仅是他的表演追求,也是他的成长轨迹。在光与影的交界处,在恐惧与渴望的临界点上,一个演员正在成为他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