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彤深情回忆《许绍雄》:导演的长文追忆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# 最后一个离开片场的人
他走的时候,应该也是一个人。我想。
这念头来得突兀,却又理所当然。就像他生前的每一个清晨,总是独自出现在片场门口,手里提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,安静地等着开门。如今,七十三岁的许绍雄先生——我们都爱叫他“欢喜哥”——独自走向了另一个片场。那里或许没有聚光灯,没有摄像机,但一定有戏。
第一次见到他独自来录节目,我有些诧异。那时我刚入行不久,对“资深演员”总有些刻板想象——至少该有个助理帮忙拿拿东西,安排安排行程。可他总是准时出现在集合点,背着那个看起来用了很多年的帆布包,像个赶早课的大学生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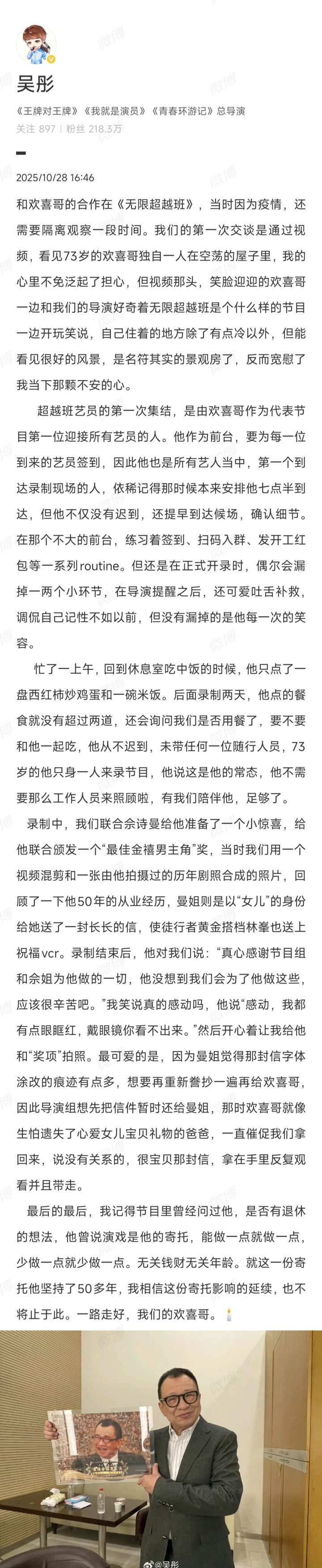
“欢喜哥,您一个人?”我终于忍不住问。
他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像老树温和的年轮。“一个人够了。”他说,“有你们陪我,足够了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这“足够”二字,贯穿了他的一生。足够的热爱,让他演了五十多年的戏;足够的知足,让他从不计较排场与身份;足够的坚持,让他在七十三岁高龄依然说“没想过退休”。
记得有次深夜收工,我见他独自坐在休息室的长椅上,慢慢收拾着剧本。台灯昏黄的光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他不是在收拾东西,而是在整理自己与角色之间的某种契约。
“欢喜哥,这么晚了,我让司机送您吧。”
他摆摆手:“你们年轻人忙你们的,我再坐会儿。”他拍了拍身边的剧本,“跟老朋友们道个别。”
后来我才懂,他说的“老朋友们”,是那些他演过的角色。每一个角色于他,都不是过客,而是住进他生命里的朋友。他从不急着从一个角色跳脱到另一个,总要留些时间,好好告别。
去年他生日,我们剧组给他准备了个小蛋糕。吹蜡烛时,有人起哄问许愿。
他认真想了想,说:“希望还能多演几年好戏。”
有人笑:“欢喜哥,您这年纪,该享享清福了。”
他摇摇头,眼神里有种年轻人般的执拗:“演戏就是我的福气。没有戏演,日子就空了。”
这话说得平淡,却让我心头一震。在这个人人谈论片酬、流量的时代,他依然固守着一个最朴素的真理:演戏不是谋生的手段,而是活着的意义。钱财、名声、年龄,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,都无法动摇这份纯粹的热爱。
如今想来,他每次录完节目最后一个离开,或许不只是因为要和角色告别。他是在用这种方式,守护着某种正在消逝的东西——那种对表演最本真的虔诚,那种把一生都献给一个行业的专注。
他走后第三天,我路过那个我们常录影的摄影棚。夜深了,灯还亮着。恍惚间,我仿佛又看见他坐在长椅上,慢慢收拾着那个帆布包。
原来他从未离开。他只是换了个地方,继续他的戏。而那些他守护了五十年的东西——敬业、朴素、热爱、坚持——已经像种子一样,撒在了每个与他合作过的人心里。
我们会记得,曾经有这样一个人,用一生告诉我们:真正的演员,是最后一个离开片场的人。而真正的热爱,足以让生命在谢幕之后,依然余音绕梁。
灯光暗下,掌声响起。欢喜哥,一路走好。您的戏,还在继续。